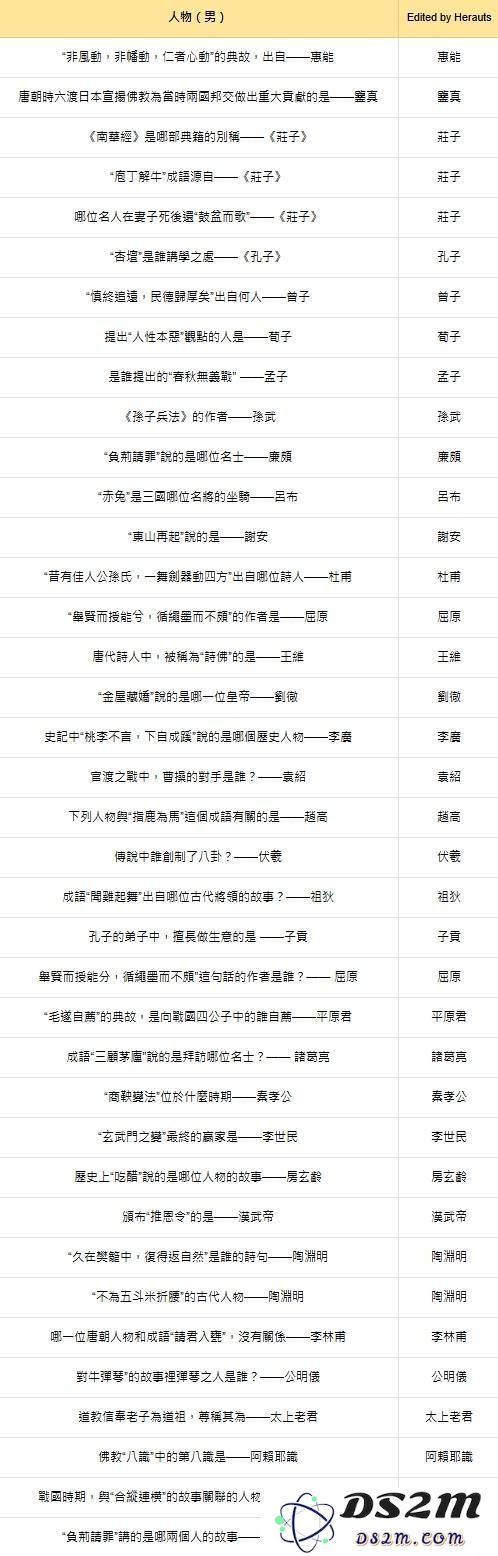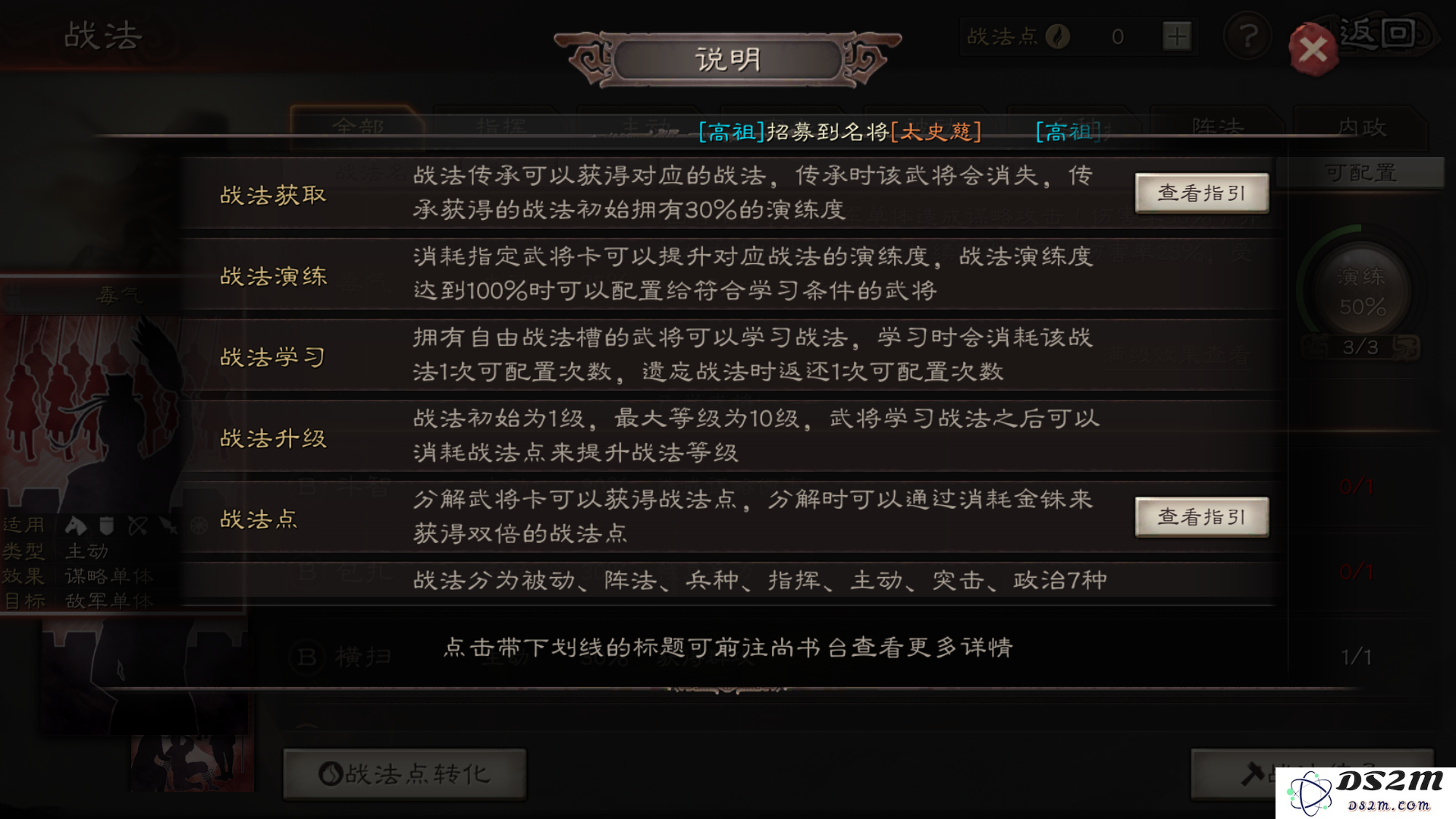建国大业的魅力——揭示媲美主机游戏的《共和国》背后的创作历程与艺术追求
■ 星星之火
“移动平台上的绝大多数游戏都让我感到厌倦、枯燥,缺乏灵感,因此我打算向自己发起挑战,着手编写并设计一款值得一玩的移动游戏。”

2012年4月,Ryan Payton携其新作《共和国》登上了Kickstarter平台,在接受GameInformer采访时,他如此介绍了自己的创作动机。人们对于他所承诺的“AAA级iOS体验”表示欢迎、质疑、愤怒或不解,但鲜有玩家会对此无动于衷——毕竟他是Ryan Payton,他为业界贡献的上一部作品是《光环4》(Halo 4)。
在过去的8年中,玩家们因“合金装备”“光环”系列作品而记住了他的名字,他曾经历过美日两国顶尖游戏开发团队的锻炼,他曾与小岛秀夫共事,在343 Industries从Bungie处接手《光环》品牌之后,他还曾为建设微软游戏事业的支柱之一而倾注自己的一份力。
2011年9月,Ryan Payton同时宣布了自己离职与创业的消息:他告别了《光环4》叙事设计师的职位,创立了新的开发团队Camouflaj,面对自己的创造力已无法动摇“光环”系列前行轨迹的现状,他将野心寄托于未来的独立作品:“有人认为我疯了,但我确实想要做出一款能够让十亿玩家共同体验的游戏,而且还要让这款游戏为玩家带来的冲击胜过一部出色的书籍或电影。”
他的野心最终构建起了游戏中的世界——以反乌托邦三大代表作《1984》《我们》《美丽新世界》为蓝本,描述极权政府对人民的严格监控,探讨权力对隐私和尊严的践踏,讲述人们在沉重压迫下进行的反抗。游戏的主角被命名为“希望”(Hope),但玩家所扮演的并不是这位主角,而是主角求助的对象——统观全局,神通广大的“老大哥”(Big Brother),它没有实体,却存在于游戏世界中的所有电子设备之中:每一部监控摄像机都是玩家的双眼,每一盏灯、每一扇门都由玩家亲手掌控。在这个充满恶意的冰冷世界中,玩家是唯一能够保护和指引希望的存在。“希望”是一位坚强到足以对抗整个世界的女性,但不是手持枪械或利刃的杀人狂,她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战胜极权政府的爪牙,而玩家也不能超出能力的限制代替她击垮敌人,你们需要彼此以经历完整的世界,通过对方的视角见证共和国的另一面,最终了解到全面的故事。

创作《共和国》的契机与游戏沉重的主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游戏最终呈现的面貌几乎于最初的构想毫无关联。Ryan Payton与小岛秀夫团队度过的时光确实为他提供了大量灵感,但主角“希望”的雏形却来自于Konami公司的另一些产品——你绝对想不到是哪些——《心跳回忆》与《爱相随》。Ryan Payton曾在1UP的访谈中表示:《共和国》理念最初的火花源自一场头脑训练——目标就是为(日本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设计一款《爱相随》。
“如你所见,虽然游戏最终与Konami的游戏相差甚远,但我最初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与内田明理(《爱相随》系列制作总监)的问题是一致的:‘我如何才能创作出这样一款游戏,讲述一个关于玩家与处于便携设备另一端的角色的关系的故事?’但在创作的起点,我并不想让‘希望’成为玩家的女友,于是我们的一致愿景至此分道扬镳……”
Camouflaj铸就《共和国》的过程就如同游戏所展示的世界观一般,一切都建立在重重矛盾螺旋之上:Ryan Payton的履历上记录着家用游戏主机平台数款大作的荣耀,供职于Camouflaj的员工也大多拥有数款大作的开发经验,他渴望能够亲自带领独立开发团队重现昔日的辉煌,但选择的平台却是几乎与AAA级游戏无缘的iOS;他计划创作一款以潜行与求生为游戏体验核心的动作游戏,但游戏所面向的输入设备却是对动作游戏存在巨大操作缺陷的触摸屏;他为游戏的开发流程规划了包括动作捕捉与全程语音的奢侈步骤,但现实中工作室的资金却极为紧张——Camouflaj为自己的事业绘制了乌托邦般的蓝图,但这份事业却因此陷入了反乌托邦之中。
当《共和国》的开发因资金问题而陷入僵局时,Ryan Payton原本打算遵循业界传统,向一位富有的开发商求援。他登门拜访了当时供职于Unity公司的Todd Hooper,谈论了自己的理想,但直接导致双方的会面不欢而散。
“我们向他描述了自己想做的游戏,并表示‘这就是我们的游戏,我们想保留这部作品的知识产权,我们想为自己的创作全权做主,我们想自主发行这款游戏,我们想找一位愿意为我们提供资金的投资者。’而对方则回复了一句‘祝你们好运’并大笑不止。他表示,‘冲你们所提的这些条件——以及这款游戏的昂贵成本——不会有人愿意在无法获利的前提下给你们一笔钱的。’”